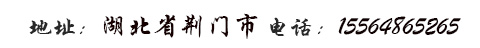割油菜王泽珠
|
HuangHeCreativeWriting 黄河文创 与您同行 (总第期) 割油菜文/王泽珠 我因了家力单薄的份,不想再种去年栽过当归的地了,想荒几年,原犁开地栽上当归,生茬易长。这个大多数人验证过的事实,或只有地质学家能解说得清楚。可妻叨叨,地还那么肥的,荒掉真是可惜,不若种茬油菜,收碾上两袋,榨一壶油,到过年的时候,咱再不出钱买油嘛。听着妻恳恳的话儿,我无言以对,只等在耕种的时节,续一茬油菜。油菜的籽,还是老品种,还是在五六年前,在老丈人家拿过来的籽。心谋着到邻里倒换上两碗,看下来咋样,却不知怎么,翻过了地,怕在给人下气上,原就种上自家的旧籽。还好吧,还好看目前的样子,算多亏妻的一片良苦用心,遂了意愿。心里这么美滋滋地想着,老天爷却处处与人作对不成,一连晴上几天,又是一连几天霪雨霏霏,可怜的邻人,只要雨一停下,忙就去了地头,为的是自己日日夜夜念着的庄稼,少被糟蹋而已。今早起来,天色依然阴阴沉沉的,烟雾氤氲于山巅,西风窜得紧,穿过屋前的断枝柳,穿过屋后的老杏树,飒飒作响。即之,泛黄的叶片是翩翩落下,一片……接着一片,那蜷在枝桠缝的瘦小杏粒,滴在角房的彩钢瓦上,发出惊魂的声音。总之,丰硕的秋已悄然欲离,或随之而来的是促人敬畏的冬,脚步沉沉有力。我裹肩儿溜在门前,被这冷飕飕的气流,原拍回屋里,似有颤栗之感。套一件穿了几年的旧棉衣,破是破,浑身倏地暖意萦拥。母亲起来后,屋后转了一阵,来到我睡的屋里——灶房,一会拿笤帚扫扫案板,一会又捏着两颗长了芽的旧洋芋,末了起身就说,让我随便做点吃的,她要到场埂子低下的那儿拾李子去,看人拾去没?我让母亲算了,价钱还那么低的,你吃吃力力地拾上几斤能卖几个元呢?母亲不吱声,直接是掮个装李子的背篼转屋后走了。或在她看来,一个无经济来源的大家儿,孩子要上学,家里得耗费,哪儿来钱呀……拾了卖上多多少少,添一点算一点么,她闲不住。我走走或坐坐,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饭食?妻此时在管念小学的小女儿和小儿子,两个大娃,在县城念着高中,这个家,惟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了。那就开始做吧,僵持什么,不吃一口,空口袋是立不住的,还要干活。于是,原削了两颗有芽子的旧洋芋,擀一薄哒面,这在草房里揽一背篼生火的草秸而准备要做些碎饭了,恰好,在场埂子下拾李子的母亲也进大门。她把装着李子的背篼立在檐角下,怕翻倒且寻两片砖塞在底面,支稳后,连着一阵“簌簌簌”地脚步声,遂进灶房坐在一条尕板凳上,往灶膛里续着麦秸,让锅里继续沸腾。等切碎的洋芋煮熟了,撒一点调料,专是下面吃饭的事。母亲说:“吃过了,我洗锅刷碗,你磨上两把镰刀,咱俩割油菜走……若老天爷变动上几天,爱生芽的油籽,全会出芽在地里了,榨不出油。”我说:“那也没有办法的呀,妈……要不,你歇在家里就别去了,照管立在场里的几百豆件,豆件湿着,天不晴,是没法打碾下的,还糟蹋大。老鼠野鸡儿雀儿不算,竟一天有二三十只土鸡在周围踅食。”母亲不肯,就说养鸡的人不灵利了,天天撵堵着,前脚儿刚走到屋里,后脚儿掉头就原钻在里面,她还没那么多时间蹲守,这些死鸡娃,一天里咕咕来咕咕去,吃不饱肚儿它们是不会走的。是啊是啊,吃粮食是小事,打伤了鸡才是大事,会造成邻里不睦呀!怪只怪害人的老天爷一天一个瞎样儿,没有要晴的迹象。我和母亲吃罢饭,仅两个碗么,母亲洗完,随手装了几个馍,一瓶凉好的冷开水,还有一张洗好的化肥袋里扯下的塑料纸,出门以防万一,像这么雨腥腥的天气,下开雨了,急急忙忙走不到家,把人会淋透的。她把收拾好的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她时常爱背的小背篼里,孤自就出发了。我反扣了后门,到场里又撵了趟鸡,然把大门锁上也尾随之后。走过一段土路,再走过一座跨在溪流之上的土桥,路就全成漫上坡的路。那还是在十年以前吧,或者说更远。庄上只要在这山头有地的人家,一户一个劳力,拿上铁锨和镢头,从土桥以上至山根里,修了一条仅能通过一辆三轮车的山道。成垧的大地,一年到收获的时候,再也不泛愁了。摇起自家的三轮车,“腾腾腾”地或用不了多长时间,车辍于路畔,开始到地里往下背转庄稼。装好,钢丝绳紧好,人座上一坐,光掌握着油门,一车可要拉十来背呢。可现在,伴随着打工潮流的漫延,人们的眼光也有所转变了,一些年轻人,或多是年轻的两口子,一个照着一个,娃儿给老爹老妈一丢,纷纷就出门挣钱。怎么说呢?反正,总比蹲在家里死守几亩薄田要好得多,不像我,我是蹴着站不起的人啦!我也曾想一个人出门在外,把地里的庄稼不种了,上工程队当个小工怎么的,一天挣上百带零元,绝不是不成问题,或说找份扫马路的或说捞垃圾的也行。我不怕苦不怕脏也不怕累,高攀什么惬意的职位,能力有限,岂敢奢求。活在这个坎上,按卯套榫,自然有留于你施展角色的舞台。但是,我一出门在外,我真是不放心我可怜的母亲啊!我的母亲濒于八旬,已算是归暮之年的人了。到娃们上学念书的时间,那么大一块空旷的院落,留下她一个,孤孤单单,冷冷清清,有了疾儿病儿,她得……想到这儿,我不敢再往下想了,不由得是转过身去,见母亲才过土桥不远处,惟影影绰绰地蹒跚在那条砾石路上,似动非动。山里的雾,此时愈压得底了,以至于我被湮灭之中,也湮没了母亲瘦小的身影。隔着朦朦胧胧的雾,伴着沟涧的淙淙溪流,或偶尔间,虫鸟唳鸣萦颞颥,而未见其身。不知不觉的,我已走到了油菜地头。油菜的地原本是哥种的地,因侄儿们有了出息,都蟾宫折桂了,不守家窝,自然,地没人去侍弄,给我就干了好事。我辛辛苦苦地耕种了几年?已忘却了。总之,我在这地里样样作物是种到了,譬说麦子、大豆、豌豆、当归……等等,到今年种的一茬油菜。油菜还奈眼,油菜就是被雨淋得东倒西歪的。上边,一顺势儿往下边倒,下边,一顺势儿又往上边靠。这该往哪儿下手呢?镰刀握在手里,转了个半圈,终于在地的上角,也就是在妻割过的一个茬口上续割了。我割了有四、五捆吧,母亲才慢慢地走到地里。她走得一身疲惫呀,顾不得湿漉漉的泥土,一屁股就坐在上面,先一只胳膊试抽出拴住背篼的绳子,再把另一只胳膊抽出。她把背篼慢慢扳到怀前,取出那个装冷开水的瓶子,拧开喝了两口,原放在背篼里,并小心地提到旁儿,支着镰刀把,起身开始割油菜了。母亲老了,腰也弓了,她每割上一会,必须展腰站上半天,然后又勾下腰去,一镰刀一镰刀地刈割油菜。大概,我俩在地里割了近有一个小时,感觉随着一阵上风刮来,有下毛毛细雨的味。怪了,昨晚刚落了一场雨,还没等到晌午……我自言自语着,更像是在詈骂。这个时候,在地埂子下的山路上,有一辆三轮车开了上来,看不到车,振得对山崖的回音“啪啪啪”直响。一阵破声破响之后,就听不到声音了,估摸这车已停在车场里。果不其然,一个胖乎乎的小伙,肩搭一根塑料绳气喘吁吁地从油菜地埂下走了上来,我瞥了一眼没认准,再没去看,勾下头就继续割着,却被眼亮的人家先喘话了:“爷,今年的油菜长得好呀,赶紧割呀。”“赶紧割着呀!你……”我先愣了一下,但倏尔是缓过神来。这不是邻村的他吗?他家的地……我又抬起头,瞅了一眼他家的那片大地,上边荒着,下边像零零碎碎地拢着几堆什么,“你们那地里今年种着什么?”“青稞呀,种的迟了,早早死了,碾了当一把鸡食……没东西的,”他边说着话,边示意让我过来抽支烟再干。我摇摇手,笑着回劝。他自个嘴上栽了一支,点着喷着烟圈儿走了。即之,他的爷和阿婆也肩搭塑料绳走了上来,一见我瞪眼珠儿笑,理应我们是同辈。有何亲戚,从何而论,我说不上,但听我的母亲说过,像老先人辈里有一点老亲戚的,好多年来,两家人路头路尾的,见了就这么称呼着。大哥是个做了半辈子生意的生意人,虽然年岁已六十好几了,但依然是屋里的一家之主,或土言说的掌柜的。还记得,他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收羊收牛收野药,到后来村民们栽起药材,他就转变了思路,开始摸索着收购药材。家里有了积蓄,置了大车,也置了小车,够得上是方圆左右的殷实的家儿了。他有两个女孩,小女远嫁外乡,大女入赘家里,他只有这一个孙子,孙子也有二十几岁,自己的娃娃也蹦蹦跳跳了,也会喊爹妈了。这么言之,大哥和大姐可是坐在太爷太婆的位子上,年岁不大,有幸容得四世同堂。他俩跟我随口笑说两句后,转身就问起地下边割油菜的母亲:“阿姨,今儿你也割来着?”这句惯用的话,他们两口子像是商量好的,都问得一模一样。“我来了……我干不动了,慢得很,蹲在屋里也闲,不如出来给娃们帮上两把,少糟蹋么。”母亲直起身展了展弯曲的腰板,叹了一口气。然又慢慢蹲下来,把割在手里的一把油菜杆,交加放在另一把油菜杆上,摁下膝盖,两手把草绳紧紧一扽,开始用力地塞草绳头了。“就是呀,阿姨,都那么大岁数了,还一天忙忙碌碌地干活着,你再要怎么快呢?”大姐止下了脚步:“我今年过来,也都干不动了,到你跟前比,算个娃娃呢……干一天都腰酸背痛的。”那一刻,大哥心里像也被感触了,也长长叹了一口气,欲言而止,怕一时下起雨来,青稞转不到车场,忙去了自家的地里。大姐呢?或真有点乏累了,才不管那么多,索性过去蹴在我母亲的跟前,两个人是头对头地唠嗑起来。母亲就数落着我们家家景不好,一年进不了多少收入,还出钱的地方多……说着说着,看她那皴如树皮的手背在失去光泽的腮帮子上是轻轻揩泪了。大姐就说,老百姓么,家家都一样的呀,阿姨,她的女子和女婿在二月头就出门打工了,屋里剩成他老俩人、孙子、孙子媳妇跟两个娃。孙子媳妇光管两个娃,他们爷孙仨务着庄稼。山地不长呀,你看,今年种的这片青稞地,竟种籽都种了一袋多,这看能收下半袋吗,还瘪得不像个粮食。孙子让她别要了,不划算。那能成吗?娃们不懂事么,挨饿受苦的那几年,牛撵天边,是不见一撮细面的,再长得不好,那也是一茬庄稼呀!母亲只是点着头,她或也湎于那种一言难尽的氛围之中,在默默回忆着她们那一代人一起走过来的苦累日子。大姐跟母亲唠罢,她的孙子已背着一趟青稞下来了,此刻,雨点比之前下得大了,也稠了。似牛毛,似幕帘。隐隐间,那靠北面的那一道道山梁上,渐而一幕一幕的素白漫来,我就猜定,一场大雨即将袭来。我嚷着母亲,让她别管什么了,得赶紧往家里走,不然,雨再下得一大,想跑也跑不动了。母亲却无动于衷,就说没什么大雨的,她有一张遮雨的塑料纸,并还使唤着我,怕雨水把我湿透着凉,她不去。我没了法子时,忙忙把割下的油菜件拢成几个小堆后,还没来得及割上两把,伴随着一阵大风“呼呼”刮来,大雨也接踵而止,忽大忽小,以至于笼罩在整个眼前。大姐背着一背青稞下来说:“走呀,阿姨,大雨来了。”随在身后的大哥也说:“走呀,阿姨,路已经滑开了。”听着大哥和大姐的劝言,固执的母亲,这才挪开自己颤巍巍的脚步,在那么难走的一段山路上。终究,那张小小的塑料纸也没能遮掩住母亲,反而被雨淋透全身。到家后,各自换上干的衣服,我开始寻柴劈柴,把以前父亲曾喝过茶的那个生铁火盆,抬在檐台上,生了一拢柴火。火焰旺旺,温暖盈盈。母亲坐在一条绳襻板凳上,我坐在另一条绳襻板凳上,我们娘儿俩就围火盆烤着、说着……仿佛又回到儿时的画面。作者简介:王泽珠,男,八零后,甘肃漳县人。忙日做活儿,得暇写写日志。投稿须知 请自附题图、插图、封面、宣传语。 请用word,标明体裁、作者简介、联系方式。 赞赏金刊文一月后全额发给作者。忌一稿多投。 邮箱:huanghewenyou .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elenaa.com/zhqhjb/6084.html
- 上一篇文章: 吃饱穿暖储藏能量,过了腊八就是年大
- 下一篇文章: 老院长一生行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