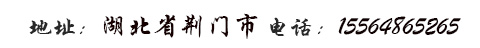求是村我的第一村第4期
|
求是村——我的第一村第4期 紫藤花开(二)——可可 “单身宿舍”那些事——可可 村头村尾——可可 微风吹过——可可 和“求是”有缘——南琳 快乐的求是人——南琳 怀念郑纪蛟——南琳 6幢记事——黄晓 7幢第一门洞——孙家鸣 紫藤花开(二) 可可 春天里,紫藤花像往年一样,藤蔓顺着小桥门把花穗儿悬在门外,散出一街的香气。起风时,花雨漫天飞扬,细细碎碎的花瓣顺着桥下的流水慢慢流淌。在那个岁月里,真诚无邪的我们,心里都留下了无法忘怀的记忆。 小说《红岩》,是我们这代人人耳熟能详的小说,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双枪老太婆这些英雄志士,让少年激情澎湃,然而白公馆,渣滓洞里的血腥与残忍,毛人凤,狗熊等军统特务的阴险也让我们毛骨悚然。求是村居然也有潜伏的“军统”就是那个烫着大波浪的阿姨,学校里的一个普通科员,好奇心被大大的激发了,马靴,船形帽,叼着香烟,是国民党女特务的形像,著名艺术家王晓棠演绎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妖媚的女特务阿兰小姐,一曲摇摆的探戈,让所有人记住了她。大波浪阿姨被双手反剪,胸前挂着用铁丝扎起来的白牌,名字被触目惊心地打上叉,一路被红卫兵高呼着口号押着穿过小桥门,紫藤花似乎也在战慄。小朋友们站在两侧的草坡上惊恐的观望。桥下水深鱼肥,低柳拂水,细长淡淡桔红的花儿轻轻摇曳,下雨了,雨水所化的一滴滴泪珠悄悄地顺着柔嫩的花瓣滑落。 那时太小了,一直非常好奇,阿姨真的是军统特务吗?于是努力把她想像成那个偷斧子的人,长波浪,高跟鞋,从不和人聊天,一直独来独往,深夜是否也在给党国发电报“高山,高山,我是大海,滴,滴滴滴,,,”发挥了一个孩子所有的想像力。 文革结束后与大波浪阿姨相邻,依然是黑色的发卡美丽的长波浪,走廊过道上相遇,总是侧身让人先行。无论去学校,去菜场,甚至去倒垃圾也是衣履整洁。一直想倾听阿姨内心的声音,在苦难中,是否困惑过,是否害怕,是否绝望,如果绝望过,又是什么让她挺直腰背,在所有人都用好奇,怀疑,不屑甚至仇视的态度打量,面对变得如此难堪,天天扫大门,扫厕所的日子里,在所有人的岐视中依然宁静,就像一池静水,波澜不惊。大波浪阿姨有一双儿女,女儿直率健谈,我们自然成了朋友,阿姨是北京人,聪慧过人,北大才女,却家境贫寒,当年阿姨极爱美,为了挣得一双长筒玻璃丝袜,也会给富家卫子弟做枪手。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国民党军统录用,主要是优厚的薪水可以帮衬父母养家。文革结束后结论:“没有直接损害过人民群众,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阿姨的先生是一可爱的教书匠,解放前留学德国,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穿一中式老棉袄,每天傍晚,双手反插在袖笼里,就像漫画中的丰子恺先生,与阿姨一前一后悠然自得的慢慢穿过小桥门去散步,除了学生偶尔上门请教,也不和人来往。 大波浪阿姨落难后依然可以用火钳烫一个长波浪,极优雅迷人。有一种人大概是不需要与人交往的,他们只与自己和书本交谈,这样的人也应该很幸福。 如今小桥门两侧已砌了水泥护栏,没有了往日宁静空旷的绿草地,与夜虫儿弹奏欢乐夜曲的青碧低矮的灌木丛。那低颓土坡上朵朵缤纷的野花,那细长淡淡的桔红的花儿都成了梦,然而我记住了花儿的名字,它叫忘忧草。 可可写于年6月14日晚8点 又:大波浪阿姨去年去世,九十高齡。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 可可那时候的模样 “单身宿舍”那些事 可可 住回求是村后,经常会遇见以前的老邻居,阿姨叔叔们都已是耄耋之年了,可是几乎每个人都会和我聊起单身宿舍的往事。那是一幢呈工字型三层楼的房子,原来是单身教职工的宿舍,后来成了家属楼,楼的东面是一个小水杉林,葱茏的树木映着中间一极小的绿色池塘,小鸡仔们在塘边找食,,荊条花障上牵牛花盛开,到了夜里塘中蛙鼓蛩鸣。天晴的时候,树之间晾晒着的被单像彩旗一样飘拂。朝西的楼前有很大的草坪,小朋友放学后都在那儿疯玩,穿过玉古路就是学校对外的一个小门,护校河从门前的小桥穿流而过。我家东西对门两间,西面正对着小桥门,中间是走廊,两边是大盥洗间,一楼有公共浴室,浴室前是一个很大的化粪池,平时扣着盖,四周绿草如茵,到了春季,那儿的荠菜长得又嫩又大,北边是员工食堂,边上的杂草野花在暮春的阳光下迤逦而开。再向北就是大片农田,大草坪与田畈之间被人踩出一条小路。小时候生病不能去幼儿园,经常会被父母反锁在家里,就趴在窗口看小桥门来来往往的人。楼下爆炒米花的老头,摇着那像黑萝卜似的铁筒,时间到了,老头一脚踩住萝卜尾巴,一只麻袋套在萝卜头上,捏把鼻涕,大喊一声“响喽”空气中就迷漫着米花的香气。这时义乌换糖佬摇着扑楞鼓“扑楞扑楞”的来了,吸引着孩子们,白布下蒙着米粉的金黄色的麦芽糖真是诱惑人,义乌佬用小铁棍抵住一头,另一头嘣嘣敲下一小块,平时积攒的牙膏皮,鸡毛毛换来的糖放在嘴里盘放啊盘的,幸福极了。 春天里几个小朋友,拎着竹篾小篮,在楼前的野草中间挖荠菜,满篮翠绿,裴琳两眼只盯着又翠又嫩的野菜,一脚踩空,掉进了化粪池,小朋友大喊“救命”路边那个鞋匠,找了一钉耙,快步奔来,气势就像那唐僧哥哥的二徒弟,就缺了两只忽扇扇的大耳朵,老鞋匠在化粪池里掏来掏去,钉耙钩住了裙子,把裴玲捞了上来,单身宿舍小朋友们都围着化粪池看西洋镜。 晚饭后,小孩子们在公共浴室洗完澡,脖子上扑一圈痱子粉,夹着芭蕉扇,麦草扇,拎竹登儿,大草坪上围一圈,旁边燃一圈气味浓烈的纸圈蚊香,享受不时吹来的一丁点儿风,如洗的月光下,大家讲一千零一夜,基督山恩仇记。随着文革的深入,不知谁讲了一双绣花鞋是从一本破烂的手抄本上看的如同鬼狐传说,草丛中有蚱蜢跳到谁的脚背上,被惊吓得“哇!哇!”的乱叫。这时孙兵与“老公鸡”这些男孩子们在黑暗里,蹑手蹑脚往田畈西瓜地里进发。附中的吴芝梅老师,同学都叫她“狐狸精”,沿着护校河飘飘悠悠的走过,穿一袭白裙,很美。 夜深了,只有公共浴室的灯光还昏昏然的亮着,睡梦中突然被大叫声,追赶声惊醒,大家都趴在窗口往下看,被追赶的数力系陈老师,已经被东面水杉林中,电线柱斜拉的钢丝跘倒在地,眼镜飞了出去,双手在地上乱抓,嘴上,額头上全是血,两个半大的孩子,手握铁棒,一顿乱棍,陈老师苍白的脸上,头发上,蓝色的中山装上,全是青苔泥巴,鼻子里流着血。三楼拐弯角上,谁家的留声机隐约传出小提琴演奏的梁祝,似有似无,无绝如缕。单身宿舍的人都知道了,陈老师被打的原因是,偷看女浴室,那两个孩子满脑子阶级斗争,他们像侦察兵一样守候多时了,好不容易擒住一个过路的。陈老师的妻子范老师是特别爽朗的人,但出了那事以后,在盥洗间总是低着头,我也不敢看她。没出几个月,陈老师带着儿子去了泰国,范老师和女儿没走。父亲叹息的说,那天晚上是因为数力系办学习班到深夜,被如此污辱,学校肯定留不住了陈老师了,真是可惜!这是一对业务能力极强的老师,天生搞数学的脑子。文革中出国是很难的事。听父亲说,陈老师的养父在泰国是有影响的人。想起小时候我常去范老师家,她总是从画着大公鸡的饼干筒里,拿早茶饼干给我。我很喜欢她,而陈老师是那种天性羞涩的人。不久王蓓爸爸也在深夜被红卫兵五花大绑带走,从那个时候就有了心思,担心父亲什么时候也被押走。医院又碰见范老师,她退休前一直在数力系做老师,如今数力系已经变成了理学院,她还像以前一样的爽朗,语速很快,精神极好。范老师的儿女很出色,陈老师却从出国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可可写于年7月原住单身宿舍二楼 可可(中) 村头村尾 可可 那个年代,伢儿们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买菜,烧饭,管弟弟妹妹,所以每个同学的脖子上都挂着钥匙。老底子求是村四周全是农田,阡陌纵横,夕阳西下时,田野里草紫花大片大片的,如轻烟一般,肩着鱼竿的老农,暮色里行走于田畈小路之间,有画中人的味道。沿着求是村的玉古路上,是煤渣铺设的路面,路边是菜场,肉店,糕团店,另一边是颓坡,坡下的护校河蜿蜒,向西而折。一株古老半边空心的柳树斜覆在河上,天热的时光,知了在茂柳高樟上嘶鸣,男孩把和成的面粉,又洗又揉的成了面筋,涂抹在竹竿稍,黏住蝉翅就俘获了这些小生灵,有一次三宝爬上柳树粘知了,树杈断了,掉进了护校河。 每天早晨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拎着竹篮去买菜,豆腐四分钱一块,卖豆腐的阿吴嫂巨高临下的,站在热气腾腾的一板板叠着的豆腐后面,手脚特麻利。黄暄儿二分钱三斤,买回家,用脸盆养在清水里,注几滴菜油,吐出泥沙,晚饭时炒一下,放葱丝姜末,蛮鲜的。最怕去买肉,肉店倌神气的像梁山好汉,刚怯生生的说:要两斤肉骨头,他就手挥板斧利器“啪啪”剔除猪肉,一堆筒儿骨“噌”的飞进你的篮子,嘴里大声喊“四角洋钿”。肉骨头八分钱一斤,本来打算买两毛钱的,这一下买疏菜的钱不够了,看着一大堆肉骨头真想哭。 最爱吃的是条头糕,方糕,还记得糕团店在肉店的隔壁,一大早,围着白围裙的阿姨将新鲜的糕团一屉屉的打开,卖糕团的阿姨温润和气,不像隔壁肉店的黑旋风,屉笼里半透明的米粉裹着豆沙馅的条头糕,上面洒着香喷喷的金黄色的桂花。而方糕是小小的木模压出菊花,海棠花,下面垫一张绿色新鲜的棕箬壳,晶莹洁白,软糯香甜,有白糖馅,玫瑰馅的,里面掺了薄荷水,夏天吃起来凉凉的。糕团店还专卖荷花糕,那是一种专门给小毛头吃的食品,几分钱一斤,买回来用大太阳晒干,贮存在饼干箱里,吃的时候煮成糊糊,放白糖,一口口的喂小婴儿,旁边站着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看着这甜甜的糯糍糍的荷花糕,馋的直掉口水。谭琳那时总给小弟弟买荷花糕,现在他在美国大学教数学。 读小学时得过肺炎,母亲按医生的嘱咐,补充营养,每天放学后可以吃一碗小馄饨,馄饨店店面极小,面对着马路对过的16路车站,柜台前面是泥地,每逢下雨积水,要抱着装馄饨的搪瓷大杯,从垫着的红砖上像踩梅花桩一样跳进去,店里的豆浆西施有着高挑的细眉,用一小竹片刮一点点肉馅,往馄饨皮子上一抹,一捏,极薄成半透明状的皮子,里面裹着粉红色的鲜肉馅,汤里撒着葱花,鸡蛋皮,撕得极细的紫菜,红的绿的黄的,再啪的来一勺味之素,喝一口馄饨汤,鲜的得来眉毛都要跌光。隔壁的求是村村花叶舒,考上中央舞蹈学院,要出远门了,妈妈泪水涟涟的问,想吃什么?她乖乖的,小声的说:就是想吃一碗小馄饨。我的同学已移民加拿大了,回忆起馄饨店的豆浆,还记忆犹存:“那浓郁香厚的美味咸浆,三分钱一碗,舍不得吃啊!” 七幢朝西马路对面是理发店,店里三个理发师,一个是同学的妈妈,丈夫是南下干部,头发吹成大波浪,呱啦呱啦的说一口山东话,求是村好多老师都是她做的大波浪。还有一个中年师傅,发型是大包头,头发向前额吹得突伸两寸再反包到脑后,用凡士林抹得又黑又亮,看《中国好声音》导师汪峰的头发,就想起他,嘴上衔着香烟,刮胡刀在蓖刀布上,噌噌两下,开始给大鼻头的爸爸许老师刮胡子,还聊天,香烟抖个不停,真担心烟灰掉下来砸到鼻子。医院看见许老师,八十二岁了,开一小车,身体挺好,鼻子也没事。最小的那个师傅,大家叫他小木坨,背后我们喊他“葛嘴儿”其实他年纪不小,就是个矮,剪个板寸头。就他对哥哥又骗又哄,用一只小草狗把我家唯一的自行车给换走了,母亲半夜听见床下哼哼声,拖出一只饭焐窠,里面的小狗狗惊慌失措的在地上乱窜,为此,哥哥被母亲暴打,看见小木坨每天骑着我家的车上下班,挺恨他的。 可可写于年4月原住单身宿舍二楼 微风吹过 可可 小时候求是村里有一个员工食堂,红砖青瓦,还有两扇大铁门,被周围的梧桐树和香樟浓浓密密的遮掩着,清晨随着食堂里悠悠飘来的盛在大木桶里的粥香,树枝上鸟巢里的生灵也开始叽~啾啾啾的醒了,一些住在校内的教师会穿过学校的小桥门来用餐,小桥门上的紫藤开的珠珠串串,散落一街香气。食堂边的大草坪上茵茵绿草,谁家的鸡们早早放出,麻栗色的母鸡身边,一群黑色,奶黄色,毛茸茸,欣欣然的小鸡仔在母鸡脚下绕前绕后,蔷薇花却一夜之间开遍了村前村后,树下的花儿竞将一段篱笆开成了一面花墙,食堂后面的大片田野里,黄色的菜花已零落,结出绿色的长荚,青葱翠碧间加杂着紫色的小朵。一只黑白相间极肥的花猫,俨然食堂的主人,端坐在房顶的瓦片上,褐色的眼睛若有所思,注视着食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一年轻的妇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捏着肉包子,匆匆走到草坪上,母亲蹲着,孩子两眼热烈的看着那只冒着热气的包子,姆妈一口一口小心翼翼的咬着包子皮,留下肉馅给囡囡吃,可能姆妈太小心了,手不知觉的抖了,只见那个香极了肉团一下子滚到草丛里,姆妈惊叫一声,肉丸子上已沾满了梧桐树上飘落的绒毛,囡囡大哭。年轻的姆妈抱起阿囡,轻轻的拍着囡囡的背,慢慢的走远。花猫轻轻跳下房顶,叼起肉团享用。远处香樟上细碎的浅绿小花香气悠然,母鸡不紧不慢,步态优雅,倦了的小鸡仔在母亲的背上适意的趴着,阳光下屋顶青瓦上影着花猫慵懒的影子,微风过,树叶轻轻摇晃,晃落鸟声一地… 可可写于年5月原住单身宿舍二楼 ------------------------------------------- 和“求是”有缘 南琳 我们,是这么一批人,从小就和“求是”有缘,求是小学,求是中学,求是路,求是网?。小时候营养不够,没阻止我们成长,包心菜硬叶子虽难下肚,却也尝到了野菜,小球藻的美味,老和山上的胡葱,大操场上的地木耳,味道也不错。该臭美的时候不会打扮,蓝色,灰色,军绿色意味着“革命”。“革命”是什么?那些时候,年轻的心在狂热,惊恐,徬徨中跳动。如果有邻里的安慰,扶持,那怕一点点,也会终身难忘。我们狂热过,可能因为平静的久了,我们呐喊过,因为抑郁的久了,但我们还是成長了,不容易啊,艰难的道路给了我们如此磨炼,我们也找到了我们的快乐。因为我们理解了,我们原谅了,我们向前看了,我们绕开了关着大门,找到了更多敞开的大门。去过了乡下,工厂,部队,上了学,出了国,成了家,nothingisimpossible!跳一级己属不易,但弟弟妹妹们跳了三级,四级,五级?。我们继承了上一辈的勤俭,诚信,又在高科技的时代充实自己,这就是我们,在求是网中兴奋的一群人,回忆不完的往事,说不完的家常话,有一句话别不好意思说,我就先说了,我爱你们,爱我们的長辈们,爱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愿己逝去的安息,健在的長辈健康長寿,兄弟姐妹们全家幸福,子孙滿堂,有机会来美国时聚。 右2高个子的女孩是南琳 快乐的求是人 南琳 我们小时候,是那么的天真,清纯,就像小溪边嫰绿的小草,又像小野花上晶莹的露珠。爱帮助人,爱参加打扫卫生,每天送来的牛奶放在一楼门口处,没人会乱拿。那时候天蓝,空气好,夜空满是星星。村子里的路上有常常晨跑的王启东教授,也有常边走边甩手锻炼的董方明叔叔。有拎着竹篮,天天买菜的师母,阿姨,也有去那个几平方米的小杂貨店,从大缸里买回油,酱油,老酒的孩子们。能够买上一块“高级”奌心“桃酥”也算很奢侈的享受了。隋秀英阿姨,張琳阿姨忙来忙去那些居委会的事。有每天都穿的烫的毕挺衣服的体面的老师,也有粗粗拉拉的,大嗓门的山东大娘,人们乐哈哈的,互相打招呼,聊家長,开玩笑。女孩子们跳绳,跳牛皮筯,跳房子,挑小木棍。男孩子们打弹子,拍片子。活跃的王爱民老师拉胡琴,唱京剧。朱老师是高高的个子,比较严肃。吴蓉阿姨很白净,福态,不多出门,更显高贵的气质。小学的严老师大大的眼睛,很漂亮。邵谊亷老师一直是我们班主任,又严格又亲切。俞老师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不了我们几岁,程老师,倪老师,赵老师,邹老师,等等老师,脑海中还存着他们年轻时的模样。那时候,一把二胡,一个笛子,一个乐琴就可以组成一个小乐队,奏最简单也是最流行的“东方红”王一义是学校黑版报的主力。王宇平,郑纪蛟,简庆闽是我们班爱搞笑的男孩,甘栽茵利嘴直率,曾伊莉文静平和,给她剪头发时,不小心剪破了耳朵上的皮,她也毫不怨我。曾国??教授家有一奌“洋味”,桌布和窗帘有漂亮的白色花边。曾妈妈亲切和蔼,是七个孩子的伟大母亲和?惠的妻子,由于七个孩子跨跃了较長的时间段,成了联络求是人的中坚力量。余惠波妈妈妈,还有外公外婆都和蔼可亲。曾住过五幢的有周荣鑫,有一个女儿叫周小红,他们很短时间就搬回北京了,还有林正,董方明,楊醒宇,赵振华,秦乃贵,庄秉,李军,等等,牟耕也是住了不長的时间。孙青萍叔叔高高的个子,走路喜欢昂着头,常戴太阳眼镜,見了我叫“小琳……”和我妈很接近的山东口音,特别亲切。我们的教授们,讲师们,把他们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浙大,尽管他们桃李滿天下,也会记着一些求是孩子们的事儿。那些干部们,也和老师们一起撑起了这个知名学府。我们这些和浙大有着深深的感情的人,在成長的过程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难而奇特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动荡,价值覌的扭曲,人心的摧残,在年幼,年轻的我们的肩膀上压上了太重的石块。心中的痛有时还隐隐发作。当时的干部救不了老师,因为他们自己也自身难保。许多人经历了厄运,说不清道不明这是为什么。谎言获取了强大的杀伤力,善心和良知却那么苍白无力。时间过去的久了,当年的孩子们現在也老了,一切都渐行渐远。好在还有很多美好甜蜜的记忆在我们心中,也正因此,才让我们又联系了,己经不住在求是邨了,还称自己“求是人”。見面很少了,聊的更多了。愿在我们心里存住那份天真,清纯,快乐,做一个快乐健康的老“求是人”。 六十年代初求是小学排练《宇宙骏马》 怀念郑纪蛟 南琳 郑纪蛟小时候就聪明,爱搞点笑,有时在课堂上会让大家忍不往笑出声耒。小时候没看出来,長大了不仅聪明能干,还是个工作狂。最后一次見面是一次偶遇,竟然成了永别。人是多么的脆弱啊,一个壮实的汉子就这么倒下不起了,再也不和我们聊天,叙旧,聚会?。那一天是在青春路,突然遇见了他,相互都一眼就认出来了,他马上叫我去他的办公室看看。天哪,这算什么办公室啊!空气中充斥着灰尘,浓浓的,刺鼻的油漆味,还有杂乱的敲打声。他全然不頋这些,就己经放上一张办公桌,开始在里面办公了。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关于扩展宽带网的大计划。让我也跟着高兴了一番。听到他生病,去世的消息,应该是跟这次見面相隔不是很久。心里的惊讶和难受就别提了。人们常常忽略对自己的照顾,当对自身无能为力之时,一切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听说纪蛟在临走前的几分钟,还在考虑,安排工作。在那一刻,生的希望仍在,仍强烈,仍然是工作,工作?,我们永远在心里怀念你,早知道如此,会拼命地劝你保护自己。那样的话,也许你今天还和我们在一起。 求是小学 6幢记事 黄晓 从我记事起就住在老村6幢了,后来看到老照片才知道进村前是住在外平舍的,求是村建好,我们该算是第一批入住村民了。 我家在6幢中间门洞2楼10号。隔壁9号住的是冀少红、冀也娜和冀洛桑三姐妹,她们父親是省教育的干部,母亲姓赵是浙大的行政干部。文革时听到教育厅的红卫兵三番五次上门要揪斗老冀,三个女儿不开门,隔着门和红卫兵对骂,煞是热闹,真是月黑风高楼不宁,姐妹花舌战红卫兵。一楼7号住的是成璋老先生,是外语系老教授,有洁癖,每天在后门外抖被单和睡衣。成老夫人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他们有个孙子叫成家印,长我一年,老拖着鼻涕,和我常在一起玩,文革中他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而成老教授不知何缘蒙冤受屈,后瘫痪在床了。老太太过去学过法律还是做过法律工作,被称为法官老太婆,也抬不起头。不幸的是我们这帮无知可恶的小混蛋还给他们雪上加霜,经常骚扰他们,用泥糊他们家玻璃,用竹竿从地板通风孔里敲他们家地板。现在想来我们那时真是一帮没天良的恶魔。在这里我要向成老先生夫妇在天之灵深深忏悔、道歉。8号里住的是王老先生,好像是机械系的老教授,沉默寡语,他夫人是6幢居民小组长。我们的大人们都叫她王师母,我们这帮小赤佬也不管辈份跟着喊她王师母。每次她一喊“搞卫生了!”家家户户大人小孩拿着条帚刮子就出来扫地除草了。两老有个儿子,大名王一义,小名叫小牛。因比我大太多,没有玩过,好象也不常见他在家。三楼11号住的是哪家记不太清了,好象是个女干部叫陈康,也有俩大我许多的女儿。12号是王向阳王向红俩兄弟,父親是无线电系的,后来一家人搬到三部去了。顶层阁楼住的雷道言夫妇,那时他们还算是一对年轻夫妇。 第一门洞1号是我的开裆裤发小,黄式平一家,老爸是电机系教授,老妈持家,式平小名叫毛毛,同我极好,他有一哥三姐,在家的是黄式加和黄式。2号住的是吕刚吕彬姐弟俩,小彬低我一届,也是我的玩伴之一。那时的二楼3号4号住的是谁记不得了,好像有对李姓的老夫妻,可能家里没有同龄的小孩可玩,就记不得了。三楼5号是我的另一发小汪力一家,他姐姐是汪红,同住还有他俩的爷爷奶奶。汪力、式平和我整日摸爬滚打在一起。记得那时式平家有张椅子的座垫是活动的,夏天藤面冬天布面可以两面翻的,这张椅子就成了我们玩地道战的必用道具了,我们仨从桌子下钻入床下,再爬过连通的各种傢俱底下,最后从这把椅子坐垫的“地道口”钻出来,把他家地板的边边角角都蹭得干干净净。汪力家隔壁6号住的浙大机械工厂的王厂长,山东人,医院的医生。两儿一女,王红象(外号象鼻头)、王红平(雅号小交儿),他们都比我大点,妹妹王红兰与我同年同班,可惜当年男女授受不亲,我只和俩兄弟玩耍,红象俨然一个孩儿头,挑头去玉泉游泳池,六一儿童节一起打半票去儿童公园玩。后来他们一家回山东了,孙青萍一家从7幢搬了过来,儿子孙卫平,外号胖子和八一,虽比我大,但人很随和风趣,我蛮喜欢和他扯空,听他扯淡。他的妹妹叫孙家鸣。 第三门洞一楼13号是杨建杨光姐弟俩,一个跳舞跳得好,一个拉小提琴拉得好。他们妈妈后来又生了一个小女儿和他俩年龄差很大了。记得杨老爸用绳子拖着小女儿坐着的童车在楼前院子里转,笑得嘴闭不上,叨叨着:“哥哥姐姐这么大,妹妹这么小。”也许就这样小妹妹起名叫杨晓。14号住的一户姓赵的老俩口,有一对龙凤双胞胎,也是比我年长很多。二楼15号是周春晖教授一家,儿子原叫周小夫,外号赫鲁晓夫,人人皆知,也许是这个原因,他改名为周一明。我们年龄相仿,也在一起玩。他妹妹是周芸要小我好几届了。他们家和我家仅一门相隔。我家是丙套,一大一中一小3间。小夫家是甲套,我家厕所旁朝北的中间划归他那边,他家有5间房。我如爬上隔开我们两家的房门上的气窗,就可以看到他家那北间里有台周教授夫妇从美国带回来的冰箱!那时候看到家用冰箱真不亚于现在看到有私人飞机一样,让我的小心脏着实扑通好久。我去他家玩时,喝到他妈妈给我的冰牛奶,那真感到是匪夷所思的饮料!牛奶居然有冰的?!周家隔壁16号是汪力姑妈住的,儿子陈阳,女儿陈燕群。两人于我算是小字辈了,由于汪力的缘故,阳阳总跟着我们玩。3楼住的好像是李文铸一家,有大宝小宝和小明三兄弟。他们住的是17号,住过一段时间就搬到7幢去了。人武部高镇雄一家搬进来,我又多了一个同龄铁杆玩伴,王志平,外号道士,我们叫他小平。他上面还有个哥哥高翔、姐姐高红霞和另一位姐姐。三楼18号住的谁就记不得了。 到文革中,不知怎么住户突然多了,又有多户搬进来,家家户户都拼住了,有的住户调整了住房。小夫家的北间又划回我家这边,他那边两家拼,我这边三家拼。小平一家搬到了我楼上12号。我家隔壁9号搬进了陈挺一家,他比我低一届,有个弟弟,他爸爸是电机系教师,妈妈是浙大广播台的。黄明黄昕一家搬入我楼下8号。式平一家搬到7-16,和王鸣王进家合拼。我家也因林正要从5幢搬进10号而搬入4号,不曾想到是和未来的浙大校长韩帧祥拼住。后来林家搬出,全琳全琅一家从7幢17号搬过来住进10号,可能直住到6幢拆掉。6号搬进了机械厂工作的赵师傅一家,他挺会动手的,曾把一棵水杉树横着种在楼下院子里,结果在6幢前长起了一片水杉林,成为村中一景。 楼里的小小孩也多了,添了一大帮60后的娃娃。1号有对双胞胎兄弟,朱敏朱捷,大家叫他们阿大阿二。两人长太像了,要看头顶的发旋来区分,双旋阿大,单旋阿二。3号是王骥程和慎大刚两家,下有3个男孩1个女孩,王欣王钊慎炼慎蔓。王家有个绍兴保姆吴妈,人极好像家里人一样,王钊同她感情很深。他长大留学旅居美国,回国探亲还带家人去绍兴看望她。韩帧祥有一儿一女,海航东红,都很老实的。赵师傅的大儿子赵良就调皮了。我和汪力那时候俨然像是6幢的孩儿王,统领着这帮小小孩玩耍。 老村的楼都是栀子花在南面围成4块园地,我们乐在其中,雨天挖渠筑垻,玩泥挖土、打弹子、笃铜板、烧树叶(号称熏蚊子)、捉癞蛤蟆和其它小生物、撵着谁家的赖孵鸡团团转……楼北面的园地就不那么吸引人了,下水道窨井茅坑都开在北面,水泥井盖大都是破的,青苔遍地。好像每次搞卫生时,这北面的场地是不被重视的,只有冬天下雪,才把这肮脏的地面变得白洁。我们可以房前屋后打雪仗,以幢为单位,划好38线拼力相博。我们6幢战团是有勇有谋的,我们用雪把开放的下水道窨井填满,再滚起3个大雪球把它围上做成堡垒,然后大家回家冲抽水马桶,把下层的雪冲走,天衣无缝的陷阱就做成了,专门引诱邻幢的孩子上当,一场雪仗的结局就以喜剧结束。 6幢和5幢之间有块大草地,原本是给5幢住的领导们一个视觉空间,实际上是老村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后来文革中“深挖洞、广积粮”时期,挖了弯弯曲曲的壕沟,我们的玩耍空间变成了三维的了,后来老村8幢在这片空地上盖起来了。老村的主干道是1、2、3幢和4、5、6、7幢之间的路。在造浙大商店和8幢时,路两边垒满红砖和沙堆,成了我们的天堂,砖堆被改建成了碉堡,有枪眼有护墙台阶上下,沙堆中陷坑密布,路两侧都是壁垒森严,成了我们的游击战和皮枪战的新战场。6幢和7幢最近,孩子们玩在一起最多,抓抓儿躲猫猫故儿,夏夜乘凉也凑在一起。7幢的男孩有马衡马群哥俩,全琅,赵乃新,小毛毛朱定勤,奇奇和培培,文革拼房后,又有了王鸣王进,何进等一批玩伴。顺便提一下,7幢的孩子名字老撞车,7幢2号陈家和3号郑家都有个儿子小名叫小弟,于是就有了“2号小弟”、“3号小弟”之分;都在一楼的两户马家,一个有儿叫马衡,另一个有女叫马珩,于是就有了“男马heng”、“女马heng”之别;式平小名叫毛毛,搬到7幢后隔壁住的朱定勤小名也是毛毛,于是就用了“大毛毛”、“小毛毛”来区分。 那时的求是村真是一个大村落,村里没有超过三层的楼,楼间空间很大,人口远没有现在这样稠密,但村民间的交融程度远胜于现在,热闹程度更甚于现在。大人认得大人,小孩认得小孩,家长知道谁是谁的孩子,小孩知道谁是谁的家长。子女知道父母的社交圈,父母知道子女的朋友群。夏夜的星空下村民纳凉摆下龙门阵,东家长西家短如数家珍。父母们的友谊延伸到小辈之间,小辈们的友情更加深了父辈间交情。我们这上下两代村民是求是村历史上很独特的群体,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人。我每次回去看望老母,陪她在村内散步,老村新村的房子早已消失了,我们只能以幼儿园为原点,边走边还原往日的求是村。我把洪保平写的求是村60年变迁史转给她看,她感叹写得太好了,她说怀念求是村其实是怀念那个时代的人和人际关系以及那时人的精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愿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求是佬儿心里永远保留着我们那时的求是村。 年7月26日悉尼 黄晓上传:幼儿园打预防针。我在排队,正在打针的是田鸣,后面的女伢儿叫陈逸辉。陈逸辉后面的男伢儿也是我的同学,叫张勇平,小名大毛,妈妈是幼儿园院长。 求是小学前 胡蓬和黄晓 黄晓胡蓬汪力 7幢第一门洞 孙家鸣 浙大求是村里住了好多人,几十年住在一个社区,几十年互相不认识。当初不是这样的,几幢几号住着谁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煞煞清楚。经常有邻居让我联系老中医哥哥看病,哥哥说不用介绍就报原先求是村门牌就晓得了。因为是个移民村,所有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没有根,各家少有三姑六婆的牵绊,也没有共同的生活仪式来凝聚和认同。大人之间神交为主,相比之下小朋友之间比较热闹。 七幢第一门洞(单元):一号马元骥(杭州)陈子雯(南京)孩子马琳,马琦,马珩(昵称小妹子)。二号住两户人家我家孙青萍(山东)毛淑心(浙江黄岩)孩子孙卫平(昵称八一,胖子),孙家鸣;另一户陈良进(浙江绍兴)任旋英(湖南)孩子陈德谦(昵称二号小弟)陈进(昵称小龙);三号郑光华戴阿姨(浙江衢州)孩子郑纪蛟,郑纪慈,郑纪滨,郑原时,郑宇航(昵称三号小弟);四号刘湘兰(湖南湘潭)和汪如泽(福建)孩子汪澜(昵称小兰)汪彤(昵称小红);五号全永昕洪纯卿(宁波)孩子全琳,全琅,全琪;六号两户合住徐振华(福建)孩子徐建时(昵称条儿),徐纯羢,另一户吴国炎(福建)孩子吴为。还需要提一下七幢第二门洞七号的马大强(安徽桐城)严征辉(杭州)孩子马衡,马群,马晔一家。文革后期,一号和七号两家互换了,两家都姓马,都是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名字读音一样(马珩与马衡),总会遇到有人咨询总要弄错。有一阵时兴学乐器,马衡和马珩都练手风琴,练习曲还都一样:每天傍晚《霍拉舞曲》。每次还不拉完整,一有疙瘩重新拉。 一号有个胖子阿姨,是操心的管家婆。我们眼里她冒凶,女主人也归她管都听她的。一天小妹子拿蚕宝宝吓妈妈,胖子阿姨抱住尖叫的女主人训斥恶作剧的我们。 二号我家爸爸喜欢种庄稼,夏天丝瓜北瓜挂满窗户,还别出心裁在北瓜上刻字:永远忠于毛主席。陈良进喜欢种植物,无花果,月季花,紫荆,合欢树都是那时候认识的。 三号小孩子多大人和气是我们的游乐场。有一期间游乐场换到电机系实验室,我和原时(小妹)一起接水提水倒水玩,后来才知道这叫双水内冷发动机。 四号是文艺之家,唱歌画画写字,内容极多,是我们这些孩子的艺术启蒙的地方。夏天,一群小孩扑打萤火虫时,四号窗口却传出多重唱的歌声,还有小提琴曼陀林吉他伴奏,有一首歌唱杨靖宇烈士的歌一直在记忆中飘荡。 五号家有电视机,求是村唯一的电视机,怎么才能蹭到看电视的机会呢?一起去五号”查火”吧,可是常常因为参加”查火”的小朋友太多了,没有被留下看电视。 六号有个广东外婆,说话宫东宫东,生猛洪亮,到六号学一句吃饭叫甲bong也很开心。 七号马衡马群是我哥哥的小伙伴,曾经给我们演过一场东海小哨兵的话剧。在一号窗前的空地上本色出演,一号家把客厅里的灯拉出来照明,这三个小伙伴全演特务坏蛋,好人是谁演的完全忘记了。 .7.20杭州 左八一孙卫平,右孙家鸣 1.“求是邨”网上家园 2.我的邻居——王宪聆 3.我在求是村长大——王平 4.儿时老村1幢的记忆——林小燕 求是村——我的第一村第2期 1.“求是邨”网上家园北京哪里医院看白癜风最好治白癜风拉萨哪家医院好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ijiqingq.com/zhqhzy/95.html
- 上一篇文章: 中药学
- 下一篇文章: 宝宝体温突然升高是真发烧还是假发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