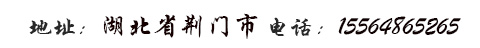岷州,雕琢的时光
|
岷州,雕琢的时光 河北·胡芳芳 岷州,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岷州,多少次在书卷里与你相遇,在花儿里与你亲热,在当归的馨香里与你缠绵,在包容冰老师的诗歌里触摸岷州,却一直无缘走近。 油菜花开了又谢,漫山的“花儿”一次次送来请柬,终于在飘雪的季节,我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01尘封的记忆飞机在石家庄腾空的那一刻,尘封的记忆大门随之洞开。 五十年代,我的父母在北京气象学院毕业,放弃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响应国家的号召,支边去了大西北,把大好的青春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边远贫瘠闭塞荒凉的甘肃。 从此,父母的半生都是在思念和牵挂中度过。 童年时,我们兄妹很不理解父母的选择,总在埋怨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生在大城市,享受优越的都市生活。多少次,父亲总是默默地叹息,被我们问急了,他只有那句话:“如果有来生,我和你妈妈依然选择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做老胡的孩子就得听话。” 因为父亲是独生子,年迈的奶奶需要照顾,在我十七岁那年,父母调回河北老家,我们兄妹也随之离开了第二故乡。在甘肃时,没有感觉到它有多美,冬长夏短,被沙尘暴肆虐得人和景都是土里土气。可是,当我们要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时,内心就像被撕裂一般的疼痛。记得离开甘肃的前夕,我和姐姐久久地在黄河边坐着,看着波涛起伏的河面发呆。 “姐,我舍不得离开,看不到黄河,我难受。” “芳芳,老家没有黄河,没有青山,我也不喜欢。”…… 我和姐姐在黄河边巨石上痴痴地看着、听着,多少次泪水迷糊了眼睛。 离开故乡的前夜,明晃晃的月亮把大地照得雪白,就像贝多芬创作《夜光曲》的那袭月光。我和姐姐在气象局大门外的小桥上静默着,凝望着远处的乌兰山顶上的皓月,聆听着不远处的黄河沉闷的喘息。 蓦然间,河滩方向传来柔婉的花儿,一对情侣在隔河对唱情歌。 “常没见着也见了,见了一面想颤了,活把人心想烂了。场里碌碡转圆了,你成园里的茄莲了,我们到一搭不须顾,立刻想的站不住……” 那歌子仿佛一粒粒小石子,砸得人心慌呢。姐姐牵起我的手赶紧跑回家。 也许是那晚的火炕烧得太热,我和姐姐烙饼一般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外屋的座钟已敲了两下。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落在墙上,就像一道奇异的时光隧道,这是在甘肃度过的最后一夜,我恨不得搬住时钟的腿,不让它奔跑。第二天,爸妈的同事朋友,我们的同学伙伴都去火车站送行,握手、拥抱……列车带着我们越去越远。 飞机上,空姐说道:“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 猛地,我从梦中醒来,收起翻浆的思绪睁开眼。飞机颠簸厉害,快要着陆了,飞机马达的轰鸣取代了记忆中列车的咔哒声。 走出机场,首先扑入眼帘的是无边的湛蓝,被金灿灿的阳光暖暖地抚慰着,安适又惬意。 02人在路上,梦在前方兰州的天空湛蓝如洗,有着宝石的清透与炫美,洁白的云朵仿佛跑到天上的羊群,悠然地飘着,引得心儿都随着它颤悠呢。清新的空气仿佛被滤过,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那一刻,我像个贪吃的孩子。这是离开甘肃三十三年以后第一次在冬天回来,温馨又亲切,熟悉又陌生。 《岷州文学》会议组派刘文珂老师带专车走了七个小时的山路来机场迎候大家,真诚热情的问候瞬间驱散旅途的疲惫,虽然初次相见,却让我们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值得欣慰的是,老哥开车来看我,在停车场,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转身,我惊呆了,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如梦似幻,呆呆地看着他,情不自禁地欢呼着去握手。转眼又是一年多没见,一直匆匆忙忙,东颠西跑,停不住脚步,以为今年无缘相聚,哪知再一次相逢。与会文友们去吃牛肉面,老哥拉着我去吃靖远手抓肉。记得上次他来机场送我,就是在这里,依然是这个店,依然坐着同一个位置,依然是香嫩可口的手抓肉,只是距离上次已两年。时间啊,流逝得好快。老哥知道我喜欢吃靖远的羊羔肉,要了一斤,他已吃了饭,陶醉地看着我大口大口地吃着,眼里满满地都是幸福。吃过饭,老哥陪我在车上聊天。牵着手说着,笑着,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别过。我们就要出发了,老哥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我趴在窗前静静地看着,太久不见,已习惯这样的静默,见了,却更想念。看来,我们真的老了,老得经不起离别...... 从兰州机场到岷县有七个多小时的车程,大巴车摇摇晃晃在群山峻岭盘行,安静地注视着窗外光秃的山丘,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思绪在时间的流里游走。 看到路标上渭源、定西等地名,我拨通了母亲的“妈,我路过渭源了。”母亲激动地说话都有些发颤:“真的吗?渭源是你的出生地啊,如果有时间去气象局看看,替我去问候一下你保姆的家人。”刘文珂看我对渭源这样熟悉,就和我聊起了这里的风景、小吃、民俗,尤其是说到当归和花儿,我们就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分享着彼此的喜悦。 夜幕降临的时候,车到定西服务区小憩。这里的气温比兰州低了很多,风吹在脸上仿佛针刺,贪婪地呼吸着清润的空气,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惬意。定西有父亲的爱徒黄叔叔和小明哥哥,打电话问候,他们很是惊讶,一再挽留。真是抱歉,远方还有期待的目光,我无法停住脚步啊。 汽车静静地奔驰着,远远地看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渐渐地闪烁的灯火汇成银河,终于抵达我们下榻的岷县宾馆。车还没有停稳,《岷州文学》主编包容冰老师带着朋友们迎了上来,大家热热地握手,无论是否相识,一样的微笑,一样的温暖。无须介绍,几乎同时我和包老师喊出了彼此的名字,终于见到了尊敬的包老师,相识两年多,在书中在电话里在文里,熟悉、欣赏、尊敬,却一直无缘相见。在酒店大厅里等待办理入住,王循礼和张广智老师纷纷前来问候,更神奇的是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我,不但叫出了我的名字,还说到我刊发在《岷州文学》的小文,就在那一刹那间,漂泊多年的心终于安定,我与岷州没有了距离,这次,我真的回到了娘家。 03品尝十年“家宴”感谢《岷州文学》让我有机会走近这片神奇的黄土地,亲近友善正直的岷州人,触摸厚重的岷州文化,何其幸运啊! 岷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在南北朝时期,被称为岷州,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就设县级建制。古为禹贡雍州之域,秦以前为西羌所居。城南有洮河山,县西"崆峒山"。发源于青海的洮河经西寨镇、十里镇穿岷州县城而过,至茶埠急转向西北于永靖县注入刘家峡水库。 今天是《岷州文学》创刊十周年庆典,从全国各地来了四十多位记者、编辑、作家和诗人,在纸媒日益萎缩凋敝的当今,《岷州文学》竟然能坚持十年,组织如此盛大的庆典活动,真是了不起。包容冰老师以及众多的陇原文友勇挑重担,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坚守着这方文学阵地,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宣传岷州,弘扬文化,让人感动。在这里我看到了执着和无私,并从中汲取了前进的力量,让我在文学之路上走得更远。 诗人邂逅岷州,是前世的缘分,岷州结识诗人,更是今生的幸运。岷山、岷江、岷归、洮砚、岷州文学等,牵着缘分的丝线走入诗卷,还有情深谊长的包容冰老师等文朋诗友,走入岷州,你会深深爱上这方山水,走入岷州,你会发现自己的文字不知不觉多了几分禅意,诗句有了骨骼,内心却多了湿润与柔软。文人,请到岷州来,让你的一腔柔情在碧绿的洮河里曼舞,在柔润的洮砚里缓缓融化...... 《岷州文学》不仅仅是一本文学杂志,更是一座岷州精神的丰碑,引领着社会风气,坚守并传承文化的精髓,让人感动、感慨、感恩! 《岷州文学》虽然是县级刊物,但装帧精美,书画高雅,诗文厚重又大气,可与省级刊物相媲美。品读《岷州文学》上你就能窥到一些岷州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捧起它,你就号住了岷州的文化脉搏,随着它走进古老而又神秘的岷州文化,你会深深地恋上这方热土。 当我站在颁奖台,捧着“岷州文学金笔奖”的奖杯,内心涌起层层涟漪。这不仅仅是奖杯,更是故乡对我殷切的期盼,我将用自己的笔去讴歌我心灵的故乡,为她歌唱,为她呐喊,我知道今生与故乡再也无法分离。 04当归花儿开“当归!”当我轻声默读这两个字,久居异乡的游子心里会不由自主泛起涟漪。 童年时,我家在渭源生活,气象局周边的农田基本都是当归,每天穿梭在碧绿的当归田里,嗅着当归那独有的药香,很是惬意。摸摸青碧的叶片,就像摸着大地的耳朵,总想贴近它,听听它的心声。盛夏,当归开出了白色的小花,采一朵放在掌心细细端详,素雅小巧,就像低首含羞的邻家阿姐。妈妈告诉我,不要踩踏当归,土里孕育着小宝宝呢。于是,我每天都要跑到当归田里,看看它的小宝宝是否出世,每天都要和当归说说悄悄话。 渭源的夏天很短,刚换下裙子,就穿上了薄棉衣。落叶时节,当归叶片变得枯黄,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农人全家老小都聚到田野里忙活着,终于看到了成堆的白白胖胖的当归宝宝,一串串,一堆堆,小山一般堆在地头,农人说着笑着,干得更欢了。我和姐姐提着两个当归,围着爸爸妈妈笑啊,转啊。 有当归,妈妈就喜欢做鱼炖肉,我和姐姐美美地吃着,像小竹笋般努力蹿高;有当归,爸爸妈妈生活更有劲了,带我们去爬老君山,给我们打野鸡、采蘑菇;有当归,老家的奶奶姥姥身体安康,爸爸妈妈就多了一份安心。 七岁时,我家搬离了渭源,多少次梦到老君山,梦到霸陵桥,梦到青青的当归田,时隔四十年,那清幽的当归香依然萦怀。多少次,我问妈妈长在地里的当归的样子,还有它独特的香味,我怕时隔太久,记不起它的模样,妈妈一次次耐心地给我讲,每说一次,她的眼睛都泛起泪光。 当归啊当归,你岁岁荣枯,年年青碧,多希望我和妈妈能像你那样,循着时光隧道走回故乡。当归啊,当归,想你了,我就打开岷海制药的当归丸,嗅嗅那独特的清香,我就回到了故乡。 05流珠的河洮河是岷州的母亲河,是黄河上游的一大支流。 据《洮州厅志》记载:“洮水源出西倾山之北,地高流激、冬不易冻,激为冰珠。”碧绿的洮河仿佛仙子的秀发,轻柔飘逸,流淌了千万年,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与众不同的洮河风光,尤其那带有神话色彩的洮河流珠奇观更是令人神往。 岷州气候寒冷,一进腊月,洮河两岸的游人接踵摩肩,游人们不远千里慕名前来观看难得一见的奇观“洮河流珠”。洮河东西两岸被厚厚的冰层覆盖,夹着玉带般的河水,蜿蜒跌宕,浪涛怒吼着奔涌远去。鳞光闪烁的河面上,各种鸟儿自在翱翔,羽毛红艳的鸟儿仿佛天空撒向大地的相思豆。 河面布满晶莹剔透的玻璃球,碧绿晶亮,就像撒了满河的珍珠,在阳光下发出炫目的亮光。冰球翻滚着,撞击着,发出悦耳的叮咚声,仿佛仙子撒下的万斛玛瑙。如果你幸运地赶上这千载难逢的景观,请一定掬一捧流珠,在阳光下细细端详,珠圆玉润,光洁晶透,冰珠在掌心微微颤动,就像一个个小精灵在与你对视。如果把这捧冰珠抛洒在冰层,你会听到玉磬般此起彼伏的美妙弦音,空灵清脆的声音撞击着你的心扉,让你如痴如醉,不得不感叹造物主之神奇。 清代诗人陈钟秀写过赞美洮河流珠的诗:“万斛明珠涌浪头,晶莹争赴水东流;珍珠难入俗人眼,抛向洪波不敢收。” 关于洮河流珠的形成,当地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洮河的上游是地势落差大,气候极其寒冷,河水剧烈撞击堤岸掀起的朵朵浪花瞬间被冻成冰珠,冰珠随着浪花一路跌宕,奔到临洮境内,形成满河的冰珠耀眼炫目蔚为壮观。还有一个说法:岷州地势崎岖,河道狭窄,水深多漩涡,上游冻结的冰块一路激荡冲到这里,被漩涡冲击碰撞打磨,像河道里的鹅暖石一样,渐渐被磨成玻璃球似的冰珠。 当地有个神话传说,冰珠乃“鲛人泪”变化的。王维新《洮阳八景》诗云:“冬日河流急,浮波珠粒粒;不劳像罔求,自有鲛人泣。”洮河流珠的形成,至今未能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 洮河流珠晶莹剔透仿若仙丹,被岷州百姓视如神物。每年腊八这天黎明,家家户户的男丁争相去洮河里挑来流珠,放在院里,家里的长辈率领众小一起赏冰珠,谁家的冰珠采得又圆又大,预示着来年他家的日子圆美,腊八全家赏冰珠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从前岷州当地有一道用洮河流珠做成的小吃叫“珍珠汤”,人们从洮河舀起冰珠,滚上面糊在油锅里炸,面糊形成硬壳包住里面的冰珠,冰珠受热化成一汪冰水,外焦内空,就像奇异的珍珠丸子。可惜,现在这个小吃几乎失传。 洮河流珠是仙子抛洒在人间的星星,是寒冬给洮河写的情诗,是天与地对唱的花儿,沧海桑田,那情诗,那清纯的花儿却更古不变。 神奇的洮河流珠,更像羽化的马家窑彩陶和洮砚,在岁月的长河里修炼了无形的翅膀和不灭的灵魂,亦或冬眠的岷州花儿,栖息在洮河里,化作冰珠,依然在歌唱,从黄土高原,欢唱着走向远方。 06精美洮砚会唱歌洮河碧绿如绸清润甘甜,不但养活了这方生灵,还给这里滋养出无价宝----洮砚,洮砚是中国三大名砚之一。 砚台历史悠久,见证了中华数千年的文明传承,学习中国的古老文化,绕不开对砚台的研究,岷州是洮砚的产地,有着千年的历史,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时闪动着洮砚的身影。 岷州的砚台从颜色上分大致有鸭头绿和鹅肝红两种。这里的山石汲取了日月的精华,得到碧绿的洮河水亿万年的浸润,有了玉的温润和水的灵秀,经过工匠巧夺天工的雕琢,终于变成妙不可言的洮砚,一年年,一岁岁陪着苦读的才子走出岷州,走向京城,走向历史的书页,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拂去历史的尘埃,你会看到从古至今,岷州的书画,岷州的状元,在中国的历史有着不可小觑的分量。造物主给物华天宝的岷州丰厚的赠礼,勤劳朴实的岷州人给上苍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洮砚的造型与众不同,别的砚台大多是单砚,而洮砚有盖,打开就是两个砚台。岷州气候寒冷又干燥,古时为了方便书生赶考,避免墨汁凝冻和风干,特设计了带盖的砚台,看似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性化的设计,却让我们从中窥到古人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岷州盛产洮砚,惠泽这里的文人,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又推动了洮砚的发展,洮砚与岷州文化就像灵与肉,朝夕不离。 一方方古朴莹润的石砚诉述着历史的变迁,我的目光久久地抚摸着那些精巧的灵石,不知不觉融化在那方砚池。 洮砚是君子,讷于言,敏于行;洮砚是女娲娘娘补天剩下的那块灵石,给这方水土以智慧和传奇。 07在“花儿”的歌海里花儿是山歌的一种,亦叫“山曲”、“少年”、“野曲”,适合田间地头劳作中演唱的小曲。它诞生于一千七百多年的西晋永嘉末年,其祖源《阿于歌》,由鲜卑族慕容部创作,传至陇上今甘肃岷县一带的土谷浑部落,被广泛传唱。主要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相邻的地区。按地域区分主要有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和陇中花儿。 花儿是岷州人的另一种语言,就像呼吸一样须臾不离。岷州人比较内向羞涩,不善表达,但奇妙的是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唱几首花儿。女人寂寞就唱歌,男人唱歌更忧愁。岷县二郎山花儿的曲调叫“阿呜怜儿”,亦称“阿欧令”,曲调起音突兀上扬、高亢粗旷,好似尖刀刺人的尖叫声,也叫“扎刀令”。 岷州二郎山五月十七花儿会最早源于岷县的祭神赛会,据考证其形成时间为明代,参与民众达十万余人,是国家级非遗。此刻的二郎山成了花儿的世界,人的海洋,从山脚至山顶歌子海潮般涌动着,来自岷州各地的民间歌手五个一伙,十个一群,对歌赛花儿。置身于情歌的海洋,你会不由自主还原到最初的自己,放开喉咙高歌一曲,热辣的歌声仿佛冬日的暖阳,唤醒沉睡的情感,被花儿抚慰过的心灵柔软丰盈。 岷州花儿的歌词非常有趣,都是乡间俚语,尤其善用叠词和比拟,却形成了岷州花儿独特的语境,把热辣、缠绵、执着的情爱推到极致,再用高亢尖锐的嗓音唱出来,即使再坚硬的心肠,也会为之颤抖。 阳坡出来火煞煞, 那是你哄我的话, 杨柳叶叶倒搭呢, 叫你把我要下呢! 远路上, 斧头垛了红桦了 你把好的行下了, 给我就打给回话了 “阿呜怜儿”,它以高亢激越、质朴粗犷、悲切凄厉、明朗爽快的审美特征,超级稳定的短句结构,诚挚动人的情感,在岷州传唱千年,曲调、歌名却是亘古不变,虽然不如青海和宁夏花儿曲调婉转多变,却保留了花儿的原汁原味,岷州花儿也是岷州文化的缩影,它是鲜活的民歌化石。 每次在网上听到“扎刀令”的花儿,心里难受得都想哭,我却像中了魔一样总也听不够。童年时,爸爸常常戴着回族小花帽,揪着耳朵唱花儿,有学来的歌词,也有父亲自编的,唱得气象局周边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围着他转。“胡家阿达,别走啦,在俺家喝酒吧!”气得妈妈直瞪眼,但他们从不为这个打架,惹得邻居的男人们羡慕不已,老胡咋就那么有魅力。 记得有一年单位派父亲和同事下乡搞路线教育,他们去了山村,村民们纷纷掩门闭户躲避。急得同事要打退堂鼓回市里辞掉差事。父亲灵机一动,亮开嗓子,唱开了岷州花儿。歌声是最美妙的钥匙,打开了一把把被岁月锈蚀的心锁。那年父亲在乡下搞了一年路线教育,几乎跑遍定西地区所有乡镇,父亲把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带到了闭塞的山乡,工作之余父亲给乡民裁剪衣服,理发,扎针治疗关节炎,教孩子们读书,却从来不要一分报酬。父亲虚心地向乡民请教民歌,时常和他们对歌,父亲自编的歌词诙谐幽默,女人们都喜欢得不得了,纷纷争着给父亲做布鞋。 是民歌让我们一家成了老乡们的亲人,是民歌让我的父母亲在举目无亲的贫瘠荒凉的大西北奉献了一辈子。花儿伴随了爸妈的青春岁月,带我走近父母那平凡而又博大的精神世界,多希望远去的父亲在深情的花儿中复活…… 花儿是有翅膀的彩陶,它随着洮河漫游,一些沉在河底化成青玉般的洮砚,写出不朽的文字,还有一些走向河岸随着青草四处漫步,走累的花儿坐在黄土梗上歇脚,化成当归迎着阳光诗意生长,给了这方生灵神秘的智慧和力量。 那些年轻气盛的花儿坐在田埂抽袋烟,喝口清茶,歇足了,站起来,打个口哨,吆喝一声,从岷州一路热热地唱着,一直唱到宁夏,唱到青海,唱到新疆…… 08流彩溢韵的陶罐说到岷州,人们大多是从毛主席的诗句“更喜岷山千里雪”得知,却很少知道它还有一张享誉世界的亮丽名片“马家窑文化”和“齐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时期时代晚期文化,距今近五千年。对于马家窑彩陶,读过历史的人并不陌生,却鲜有人知马家窑彩陶遗址在甘肃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年被瑞典考古学家发现并挖掘,年甘肃博物馆发现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 马家窑彩陶分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器型主要有壶、罐、瓶、钵、盆等。先民们就地取材多为细泥橙黄色陶制,表面打磨得光滑细润并绘以彩条、带纹、圆点纹、水波纹、漩涡纹、方格纹、人面纹、蛙纹、舞蹈纹等日常生活中的图案。图案设计构图严谨规整,笔法娴熟老练又洒脱。线条优雅精美又流畅,条带曲折舒展有着行云流水般的韵律之美,构成了典雅、朴拙、大器、浑厚而又神秘的艺术风格。 大约在公元四千年,在洮河流域出现了齐家文化,这一时期的制陶业比马家窑文化有了明显进步。有些罐类和三足器印有篮纹和绳纹,有双耳罐、盘、鬲、盆、豆等,以双大耳罐和高领双耳罐最富有特色。 马家窑文化和齐家窑文化把中国的彩陶艺术推到最为辉煌的巅峰,它就像中国的百慕大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学者钻研考古。走近古老的彩陶,你会被它的美深深折服,从此,你的眼,你的心,你的魂,都被它缠绕着,沉醉不知归路,细细解读岁月在器具上刻下的密码,一点一点挖掘着灵魂的隧道。 文化是历史的缩影,时代的一面镜子。马家窑文化反映了新石器时期华夏文明的高度,折射着中华先民在远古时代的文化成就,马家窑文化不仅包含着史前时期众多神秘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同时它创造了中国画最早的形式。 马家窑彩陶的绘制主要以毛笔和墨作工具,以线条构图,由此奠定了中国画的发展基础。彩陶是中国文化的根,是书法绘画的源,马家窑彩陶创造了绘画的许多表现形式,形态各异的器具,神秘玄妙的图案,一个个陶罐一张张口,无声地诉说着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沉默的黄土经过先祖们的揉捏抚摸绘制,终于有了灵魂,走入时间的深处,修出不灭的灵魂,傲然地注视着世界。马家窑彩陶不仅仅是中国画的母体,细细揣摩那神秘的图案,你会从中找到美妙的旋律,把耳朵贴在陶器上,你会听到泥土悠长的呼吸,仿佛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呼麦,春潮般有节奏地涌动,一缕一缕缠上心头,催出心底蛰伏的岷州花儿,从唇齿间滑出。 我的心久久地停留在彩陶那神秘图案和唯美的造型,遥想着那一双双慧眼和神奇的手,只有诗意和禅定的心境,才能创造出如此大美的器具。古人的视野有多辽阔呢?山川、河流、星月尽收笔端,他们的眼界和心境比宇宙还要浩瀚。美来自生活,从泥土中生长出的美,才能修炼出不朽的生命力,虽历经千年,依然美得令人窒息。 09遥望岷山雄伟的岷山,不仅仅是一座常年积雪不化的高山,更是人们心中的丰碑。“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说起岷山,人们脑海里首先闪现的就是毛主席的这首诗,岷山,是华夏儿女仰望的神山,它的伟岸,它的神秘,无不令人神往。 当我迎着冬阳张开双臂扑向岷山时,我看到一朵朵祥云在升腾,山顶那皑皑白雪仿佛洁白的哈达,双手向上虔诚地叩拜,仿佛接过雪山赐予的哈达。高耸入云的岷山在这里屹立了亿万年,见证了无数兴衰,风起潮涌,云卷云舒,有些人秋叶般飘过,有些人却铭刻在岷山的灵魂里。岷州、哈达铺、腊子口,这里有诗情,有画意,更生长着红色的种子。 年9月,红军经过四川进入岷县,攻下天险腊子口,在这里修整了57天,创下了长征路上修整最长的记录,因而岷州也被称为“红色加油站”。在岷州,随处可见红色遗迹,关于红军的故事这里的男女老少耳熟能详,说起敬爱的毛主席,说起亲人般的红军战士,老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尤其说到刚从岷山翻越下来的战士,步履蹒跚,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却依然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令人敬重和怜爱。 被称为鬼门关的腊子口,两侧悬崖峭壁,一条小河跻身而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却被红军一举夺下,石堡、弹洞今犹在,侧耳倾听,似乎还能听到当年鏖战的枪炮声。红军突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召开了重要的哈达铺会议,毛主席作出“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 在岷山,在腊子口,在哈达铺,脚步轻轻,我的灵魂走在朝圣的路上。红军在这里修整,洮河、洮砚、彩陶、岷归还有岷州花儿,一点点,一丝丝,一缕缕融入红军的血脉里,终于锤炼成一支颠不垮,砸不烂的钢铁队伍。 10再见了,岷州阔别甘肃三十余年,梦里梦外都是它。 一次次踏上这片土地,一次次挥泪别离。家人朋友一次次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去甘肃?一年年候鸟般乐此不疲地回归着。远在天边的黄土高坡留下了我的童年,少年,有我一生追逐的梦想。 岷州备受老天爷的独爱,青山秀水,生长着画意,流淌着诗情,这是一个来了就舍不得离开的地方。 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胡芳芳,笔名叶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会外联部主任。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五期作家班学员,《散文风》责任编辑。创作有散文、诗歌、文艺评论等文学作品多万字。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elenaa.com/zhqhjb/7300.html
- 上一篇文章: 吃土的日子
- 下一篇文章: 内藏福利敖夷的捏土造人之术,原来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