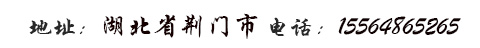又见东垣之升阳散火汤案
|
这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患者,二十多岁的女性,刚就诊时自己也没说得了什么病,有什么不舒服,就让我赶紧看看吧。我一看患者虽然年纪轻轻,但是面色很不好,整个面部中轴线上发青发暗,用那句俗话说“印堂发黑啊,撞见鬼了吧”,再看患者眼睛略突,神色外露,似有惊恐状,我说“你最近是不是撞见了不该撞见的东西了吧”,她一听顿时觉得很神密,然后点头说“最近老家邻居去世了,确实是撞见了一点东西,家里人都给请了巫师给施了施法来着,感觉好一点,但是还是害怕,已经有一周不能睡觉了,前几天几乎每天晚上都是睁着眼睛的,这两天也还是睡不着”,我打断的问了一下“是多梦吗,白天犯困吗”,“不是,根本就没睡着,哪有什么梦不梦的,白天倒还精神,不耽误干活,就是稍微有点头晕,你快给看看吧!” 我接着打量了一下她全身上下,面色除了中轴线发青发暗外,整个面色也是蜡黄蜡黄的,没有太多光泽,鼻头比起印堂来说更青暗,再看舌象是淡淡的,略微有一点偏淡红,舌上也没有什么苔,一搭脉略微有点沉弦,别无其他发现。再问一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症状,什么饮食、二便、出汗啊都还好,月经平时偏少一点,有痛经史,没有什么白带。我开始思索,正心里开始捉摸不定的时候,旁边另一人说“要不你先看看我手心热怎么回事”,“我手心也热,脚也热,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更热”这患者也插上话来,一边说一边还让我摸手心,我一摸还真是很烫。于是我迅速从我脑库里搜索到了“升阳散火汤”,原本东垣大师不就是用来治疗手足心热的嘛,而且我记得东垣说因血虚的问题,当时很无法理解,既然是血虚的问题,又用了一堆发散药(传统意义上的风药),不是更伤津耗血嘛,所以一直暗记在心,遇着这种病人一定要尝试尝试看看效果怎样。这下把我也高兴坏了,终于有机会尝试一下这个名方了,于是我就按原方给开了,柴胡9g、升麻9g、葛根9g、羌活9g、防风6g、独活9g、炙甘草3g、生甘草6g、党参9g、白芍9g,3剂,配方颗粒,水冲服,日一剂。 我很期待这三付药下去的功效,回家后还特意打开了脾胃论复习复习了一下原文,“治男子妇人四肢发热,肌热,筋痹热,骨髓中热,发困,热如燎,扪之烙手,此病多因血虚而得之。或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火郁则发之。”虽然当时还是搞不太懂这个“阴火”为什么不能直接通过补脾胃,或者滋津血来治,而选择这样一种发散的方法,还是等等这个药效看看吧。3天后,患者神采奕奕的过来告诉我说,“我的失眠好了,现在都睡不醒了,吃了一付半药以后就这样了,还真神”,我也觉得挺神的,再看患者面部中轴线上,印堂处青暗已经相当不明显了,但是鼻头部还是青暗的,手足心还是偏热,但是已经不能影响到患者的正常生活起居了。 这个时候我一方面叹服东垣的道行高深,一方面开始反思,从这个患者来看,血虚的问题是很明显的,诸如面色蜡黄,月经量少,失眠啊,都无一不支持血虚,但是若果从常规意义来说手足心热,我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阴虚,但是无论是阴虚、血虚,使用风药发散总感觉是不合规的,因为我们常规认为风药能胜湿,阴血类似于湿的液体,风药自然也能伤阴耗血。对于阴虚来说,我们肯定是会慎用风药的,因为阴虚火易旺,阳易亢,亢阳雷火都在上浮着,哪还能用风药去升阳啊,耗散啊,如果那样不得风火相煽了嘛!血虚这个问题,似乎也是这样,好像也应该摒弃风药。但是若果细想一番,道理远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血是怎么回事,《灵枢·决气》:“何谓血?岐伯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可以推知这个血的形成关乎中焦,存在一个“受气”与“取汁”,以及“变化”的过程,总得来说是血离开气是不能生成的,但是若果只有气,而没有中焦这个“汁”也是无法生成的,至于后面的“变化而赤”的问题是否仅仅关乎脾胃的问题,可能答案是不对的,至少我们目前现代医学知道血的生成离开不了肾,我想这个变化而赤的问题是关乎肾的气化问题,或者说是元阳的蒸腾变化的问题。所以现代医学一些疾病诸如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血液系统疾病,有些学者主张从肾治疗,我想是很有必要的。话说回来,这个血关乎上面三个步骤的问题,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滋阴补血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唐朝以前的本草,对于“当归”这样一个我们现代认为很平常的一个补血药,却只字未提补血的问题,而《神农本草经》首提的却是其“主咳逆上气”的功效,实际上是关乎气逆的问题,《别录》说其“温中止痛,除客血内塞”,实际上就是活血的作用。而后来唐宋的四物汤一出,后世就逐渐归类于滋阴养血类了,以至于让后人渐渐淡忘了血因气生的问题。你四物汤养血补血,难道四君子汤就养血补血了吗?四君子汤原来用于“治荣卫气虚,脏腑怯弱,心腹胀满,全不思食,肠鸣泄泻,呕哕吐逆,大宜服之。常服温和脾胃,进益饮食,辟寒邪瘴雾气。”别忘了还有荣气虚不是,再说你再回想回想你的那些用四君子汤的病人,气虚都已经那种程度了,难道真的没有血虚的问题吗,当然是有的。那为什么人不直接用上八珍汤,那个多好,又益气又养血,这个你得问问人家脾胃啊,人家脾胃虚成那样子了,自己中焦那点津液都难以化了,还有点四物帮人家增加的津液,那一用准得壅在胃脘中焦,受气都少了,取汁谈何容易,也就是说这个取汁是在受气的前提下完成的,人家受气少,怎能取那么多汁来生血,这点从当归补血汤来看,更能明白受气比取汁更重要。 再来看这个因血虚而生的升阳散火汤证,这个汤方如其名,除了参、芍、草之外,都是风药,干嘛使呢,自然是升阳散火啰,东垣认为是阳气郁于脾土,那么是因为血虚导致阳气郁于脾土,还是阳气郁于脾土导致血虚的呢,从东垣原文来看说是“此病多因血虚而得之”,看来是因血虚阳气郁于脾土,既然可以用风药升散,自然中焦的津汁不是太亏,否则还是那个风胜湿的理论,血更无以生,那么津汁够用,却不能生血,是不能变化的问题吗,如果是的化,那得补肾助阳,显然不是这样子的。只剩下一个受气的问题,这个气是不足吗,若果是怎么不用四君子或者是党参、黄芪等药直接补气不就得了,怎么还用一堆风药,这样来看这个气并不是特别不足,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关键是这个“郁”字,郁于脾土中的阳气是到不了中焦的,自然不能去受气取汁的,郁于土中,自然得升举出来,这个升举过程中难免会消耗津血的,所以适当的佐治了一些参、芍、草来固护阴液。这个过程只是解决了阳气郁于脾土不能生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血虚为何阳气会郁于脾土的问题。 那么血虚为何阳气会郁于脾土呢,我们知道“气主煦之血主濡之”,血本来是用来濡润脏腑肢体百骸的,血中自然是载着气的,血多自然载的气就多,血少载的气就少,所以血虚的情况下是阳气浮在外面,这个时候如果外形受寒、内体饮冷,阳气就很容易被郁,轻者郁于脾土,重者郁于筋节骨髓而为病。郁于脾土当升散,郁于筋节骨髓当然也应该升,所以张仲景用于治疗“诸肢节疼痛,身体尪羸,脚肿如脱”的痹证方桂芍知母汤,不是也用了防风不是,只是郁得更深,更容易化热,所以还用了知母清热。这样来看,东垣原来也是传承于仲景啊!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elenaa.com/zhqhzy/7492.html
- 上一篇文章: 老中医整理的个秘验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