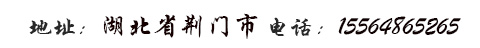又闻苜蓿香
|
李军,合阳人,中国食文化传播使者、市作协会员、李军伊尹文化工作室负责人。 又闻苜蓿香文/李军阳光肆意的播撒在田间地头,风是微风,将冬的寒冷涤荡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春姑娘欢呼雀跃般,呼啦啦一下子全涌了出来,红了桃花,绿了柳树,大地也变得活泛了,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家乡的春天,是苜蓿芽芽起的头。看远处田间地头上的苜蓿地,胖胖的小苜蓿探出了绿色的小脑袋,奶白色的根茎,绿的发亮的叶子,一棵都有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古人讲究“不时不食”,而三月初正是吃苜蓿的好时节。苜蓿俗称“三叶草”,因丝绸之路的开辟,苜蓿在汉代来到中国,张骞、汉武帝和陕西西安,一直是关于苜蓿的主题词。故而周王《救荒本草》记苜蓿,说的是紫花苜蓿,也说:“苜蓿出陕西,今处处有之。”东晋道家、医学家葛洪《西京杂记》云∶“乐游苑多苜蓿,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怀风,又名光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宗说:“(苜蓿)陕西甚多,用饲牛马,嫩时人兼食之。有宿根,刈讫复生。”苜蓿是多年生开花植物,既耐旱耐寒耐热,又能改良土壤,生长茂盛产量高,最适合做牲畜饲料。唐孟诜《食疗本草》中称,适量食用苜蓿,可使人瘦,身轻体健。但古时亦多有南方人认为,苜蓿无味,不以此为食。苜蓿含有大量的粗蛋白质、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B族维生素,维生素C、E及铁等多种微量营养素,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苜蓿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俗称“牧草之王”,耐旱耐冷耐热,一年可以割三茬,庄农人分别叫头茬二茬三茬。春头上,正当人们忙着上粪种春田的时候,头茬苜蓿的嫩芽已经悄悄钻出来了。绿意袭人。苜蓿鲜嫩无比,惹人喜爱。顿时让人眼界大开,心情舒畅。蹲下身不由得就想撅上几把,回家好好吃一顿拌苜蓿。苜蓿每一根细茎上面,有叶三齿,如倒心形,先端稍圆或凹入上部有锯齿,叶的表面呈浓绿色,茎梗极短,吃的时候,以叶为主,苜蓿与普通蔬菜相比,苜蓿的营养价值很高。维生素、蛋白质等含量通常高出1~2倍,苜蓿还有普通蔬菜没有的药用功效。苜蓿中含有大量的铁元素,因而可作为治疗贫血的辅助食品,苜蓿中所含的B族维生素成分,可治疗恶性贫血;此外,苜蓿还含具有止血作用的维生素K,成分之高,驾乎一切蔬菜之上。民间常用来治疗胃病或痔疮出血,有些验方用它来治胃或痔、肠出血。曾几何时,人们的饮食偏向了田园风味,更有各种农家菜登上了大雅之堂。在丰盛的海鲜山珍之中,再加一道时令的野菜,不仅消解油腻而且营养、时尚,也给酒桌上增加了许多的话题。惊蛰后,苜蓿嫩芽从地面钻出,大人小孩都迫不及待地提着篮子,拿着小刀去掐苜蓿,大人们指甲坚硬,直接用手指掐。这时的苜蓿虽然新鲜,但是比较少,苜蓿地里星星点点,掐满一篮子还是不容易的。但只要磨下性子静下心,想掐多久掐多久,想掐多少掐多少,天管不着,地收不着,只要你勤快、耐心就好。苜蓿有很多吃法,咋吃都不失可口,拌上面蒸,就是苜蓿麦饭,蘸上酱醋辣椒油调的蒜汁,忽而口生津液,味蕾大开,吃在嘴里绵香适口,是一个季节的口福。而做为凉拌菜,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汆水后凉拌,一种是切碎后加葱丝,炝辣椒,滴入米醋凉拌。不管哪种吃法都很下酒,也很费馍。苜蓿菜可以做汤,除了咸面汤,清水苜蓿是一种境界,水烧开,磕上一颗鸡蛋,撒上一把新嫩的苜蓿,什么调料也不放,品嚼着那种淡淡的草香,品着那如翡翠般的清水,其口感绵甜,荡气清神,任檐下杏花习习,落英纷纷,心中沉浸春风,滋生淡泊。郊县有一位朋友在自家院子就有一畦苜蓿,不为别的,只为吃菜。有一年三月去他家,她母亲执意要给做苜蓿面片,一把新鲜的苜蓿芽,硬是在案板上剁成粉末碎,然后和在面里,擀成面片,柴火水烧开煮面,煮出来在面片蘸上辣椒油蒜汁,吃起来要比白面片片要高级的多。一碗热乎乎、酸辣辣的”苜蓿片片“,再喝上一碗翠绿的面汤,很是过瘾。儿时的记忆已远去,故乡的那片苜蓿地也早了无踪迹,唯有那美好的画面偶尔还出现在眼前。每看到市场上有苜蓿菜售卖,人们趋之若鹜争相购买,儿时的味道便让我口舌生津,又一次想起了那片记录了我欢乐少年的苜蓿地了。庚子年春于弥阙斋(图片来源于网络)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helenaa.com/zhqhyl/5138.html
- 上一篇文章: 中国羊地理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